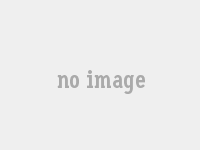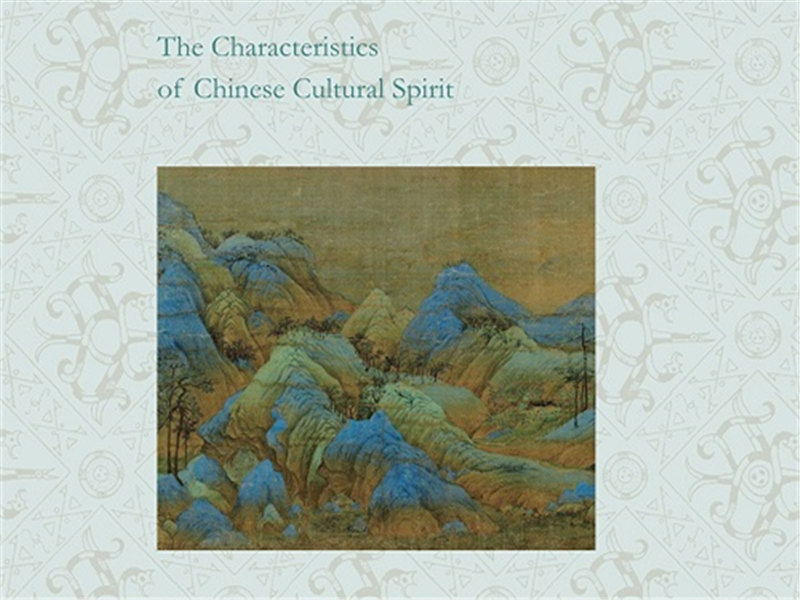今年是林散之先生诞辰110周年,不知不觉林先生已离开我们20年。前年赴川,出于对林先生崇敬,我们一行攀登上峨眉山上的金顶因为金顶上有林先生的题书。岂料重新维修后的金顶,原由林先生题写的“金顶”二字的石碑,已被移置到顶下电缆车的出口处,在导游的引领下,云雾缭绕中,我们寻觅到这块石碑。千里之遥,大有见碑生悲之感!山人的无知让我产生了一系列莫名的联想,现时的人们可能太多注重形式上的金碧辉煌了,他们不知林散之恰是中国当代书坛的一座“金顶”,他们忽略了林散之雄秀书风与峨眉风景以“雄秀”名天下的和谐统一,这种天地自然和谐的大美,才真正蕴含着时代人文精神的内在金光!
我痛心林散之离我们的远去,因为如今的年代,书坛已难再觅荡漾于俗欲之上的具有本真气息的书法,宣纸上尘土飞扬已无创造之意趣可言。我想这正是我们今天要纪念林散之,研究林散之的意义所在。
一、特殊年代造就了林散之,林散之的横空出世将中国书法艺术提升到一个令人惊异的高度。
众所周知,上世纪七十年代,经过文革十年,古老的中国正处于文艺全面复兴的新时期。以毛泽东、周恩来为首的国家政治高层在外交政策上开始松动,“乒乓外交”已成为缓和长期敌对的中美、中日关系的时髦话题,而对东瀛日本,这个有着深厚书法情结的国家,“书法外交”自然摆到了一定的议事日程。作为对日本一种民间交流的形式,1972年《人民中国》画报出版了中国书法特辑,刊登了一批中国书法家的作品,林散之的草书作品毛泽东词《清平乐·会昌》,经郭沫若、赵朴初、启功等人的审定首肯,被排在了首页。他“能代表中国”的书法,一时在日本产生很大反响并波及国内书坛。林散之由此声名大振。其实林散之被挖掘出来是很不容易的。一是他赶上了政治外交政策开始松动的变革好时期。二是他得到了既有政治声望又有高深文化素养的郭沫若、赵朴初等人“伯乐”式的认知。这些“伯乐式”的权威,如今已相继作古,难以再生。三是那个年代还没有多少市井功利,还没有官方书法组织的垄断和艺术流派的门户偏见,人们更多想到的是国家的声誉,这就自然为林散之的横空出世创造了“天时”。林散之出名时已是75岁的垂暮老人了,作为新时期文艺复兴的中国,紧接着,他又荣幸的最早以书法家的平民身份成为参加全国政协会议的代表之一,他的名字和当时中国政治高层人物一起,被国家主流媒体的电台、报纸播送、刊登。其名不彰的林散之终于被国人尽知,他的书法得以彰显,他的书法在世界上代表了中国,在中国代表了一个时代。一个垂暮老人的横空出世,同时也使他平实的人生蒙上了传奇色彩。
林散之的传奇般的横空出世,看似偶然其实是一种历史必然。避开政治因素,就他的诗书画艺术的造谐而言,林散之出名的迟早只是一个时间概念而已,因为林散之不是一位靠政治嫁接得以存在的艺术大师。他的天赋,才情和勤奋早已成就了他的艺术。林散之的晚成,恰是他积几十年功力后的“厚积薄发”。林散之青少年时代就打下了雄深的诗文和书画功底。下列事实可窥一斑:林散之五岁画虎,12岁已能为乡邻写春联;13岁前已读完儒家经典之书《百家姓》、《大学》、《中庸》、《论语》、《孟子》、《左传》、《古文观止》、《古文词类纂》、《诗经》、《唐诗》;23岁,也就是1923年,他在上海权威书画杂志《神州吉光集》上发表书画作品。其书法对联:“随意而安因树为屋,会心不远开门见山”已经初显才气。29岁完成《山水类编》29卷的编纂,全书35万字,分门别类汇集了前人有关山水画的论述;37岁孤身作万里游,经苏、皖、鲁、豫、陕、川、湘、鄂、赣十省,行程16000余里,得画稿800余幅,诗164首;39岁写成《漫游小记》,连载于上海《旅游杂志》,其文笔之典雅,文采之粲然已非常人所能为!这些事实的存在都是他后来能够成为一代大师的前提。
林先生曾向我出示过他大概19岁时临写的晋索靖《出师颂》的章草临本。他说这本法帖是他的恩师张栗庵送给他的。在我的印象中,林先生临写的《出师颂》,大量删省了章草富有隶书意味的“捺”的写法,他有意识的回避了这种“程式化”,用今草便捷的折笔连带取而代之,从而突显了今草明快灵动的特点,使自己的临书具有“自我之境”。这种天才的“变通”显露了他青少年时代的艺术才华。
林散之早年失怙,青年失聪,老年归隐江上村,不幸又蒙“汤锅之难”,他曲折的人生,丰富的生活阅历,扎实的诗文功底,得江山之助的宽广胸襟,成就了他的艺术。他的横空出世,也是中华文化在新时期开始复兴的标志。
二、研究林散之,把林散之放进几千年书法历史传统的长河中去考量,林散之亦无愧“草圣”的地位和里程碑式人物存在的意义。
中国书法的历史,是一条几千年流动的长河,这条大河有时泛起的浪花光芒照人,有时也泥沙俱下,混沌不清。审视历史也应保持警惕,学会以批判的目光面对。特别是一些书法被当作传统权威化或转换成权力的话语工具时,传统便会被一个隐蔽的巫词左右人们的存在了。基于这一点讲,中国几千年出了无数的书法家,但真正能够彪炳千秋的寥寥无几。林散之则不容置疑地列属其中。在草书发展史上值得提及的应该是王羲之、张旭、怀素、黄庭坚、明末清初有以王铎、傅山、祝允明、徐文长、陈白沙、黄道周为代表的群体,现当代仅只于右任和林散之二人。
王羲之变章为今,在张芝的基础上经增删,创今草,从而实现了真正意义上的书法变革,王羲之为代表的原创体范,奠定了今草发展历程中的第一块基石。两晋降而至南北朝,至隋、至唐。只有到唐代才出现“颠张”、“醉素”两位大家。旭、素在王的原创基础上,把草书在情意发挥上推到了极致。王羲之的伟大贡献,不光是创造了今草的模范,更重要的是他“肇乎自然、见诸本性”的艺术观,给书法注入了精神层面的生机。魏晋的书法是“玄学”盛行的文化折射,在这样的文化背景下,书法铸就了“魏晋之魂”。书法从此开始崇尚人的本真精神。应该说唐朝的张旭、怀素的大草是体现本真精神的,他们二人应是草书发展史上重要的里程碑式人物。
唐至宋,宋以行书成就最高。“苏、黄、米、蔡”,黄庭坚在草书方面成就最高。黄庭坚应是草书发展史上的革新派人物,他试图打破草书的意理结构,他凭才情大开大合,但偏失草书意圆之理。黄庭坚属权力场中的文人,以儒学为基础的权力意识在从政文人身上往往贯彻一生。“黄草”的紧紧环绕中心,由中心向两边大开大合的作品结构,是中国高度稳定的传统权力结构在书法文本中的移植。黄主张的“道义”在先,他所言的“道义”其实是与权力结盟的儒学“道义”,这与艺术之为艺术的魏晋的本真精神相背离。“黄草”逃避不了被中心力量的整合,看似夸张的用笔只是他的表面形式的存在,他太注重秩序和既定的规范。林散之曾批评黄书用笔处处讲究,这是对黄的不认同之处,恰好显露了林与黄在艺术观上的差异。苏东坡的评黄值得玩味:“以平等观作欹侧字,以真实相出游戏法,以磊落人书细锁事。”苏指黄“欹侧字”实施的是“游戏法”。元代的草书家鲜于枢评黄更是一针见血:“张长史、怀素、高闲皆善草书,长史颠逸,时出法度之外。怀素守法,特多古意。高闲用笔粗,十得六七耳,至山谷乃大坏,不可复理。”鲜于枢此说,认为黄犯有失理之病,这个“理”应指的是作为大草之书,不能有违魏晋人倡导的“本真”之理。基于以上论述,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林散之自云的草书“以大王为宗,以释怀素为体,以王觉斯为友,董思白、祝希哲为宾”,他所指的以大王为宗,宗的是王书以情性至上,肇乎自然,率性天成的魏晋人的书学要旨。他以释怀素为体的“体”,就是“草以点画为情性,使转为形质”的体。在此有必要谈谈于右任。于右任和黄庭坚的共同点是都属权力场中人,于试图将草书标准化的做法,与黄庭坚书法环环相扣,围绕中心有意识形态方面的相谋之处。黄庭坚和于右任试图革新大草的探索精神是值得肯定的,但他们都跳不出自身的局限。于推广的草书标准化,客观上忽略了草书创作的多样化和生动性,有悖于晋人倡导的书以情性至上的共理。林散之较之二人的觉悟就在于他始终秉承“肇乎自然,见诸本性”的精神层面。于右任以碑法入草,虽有厚重博大之优,但“于草”尚存碑书原本的拙拗生硬的“俗迹”。“林草”植根于碑,游离于帖,其可贵处在融碑意于笔端,不留痕迹地通过沉稳平挺的线条加以表现,从而实现了“蚕之吐丝,蜂之酿蜜”的羽化式升华。
实事求是地说,林散之上世纪70年代前的草书,虽有自我之境的体现,但仍在乎书意,七十年代以后至晚年,他的书法语言已不在像此前那样教条守中,有设计之嫌的文本结构和技术性线条,已被“刚柔相摩、阴阳想荡”的自如生发的笔墨运动所取代。特别是70年代中期往后的作品更是游离于率真与天趣之中。林散之无疑是个智者,他能批判性的从传统中汲取与创造想宜的力量,又能自觉地从传统中抽身而出,从而使他的艺术生命得以向可能的世界自由绽放!
在此值得一提的有两位人物,对林散之天真烂漫“刚柔相摩、阴阳相荡”之大草的成功起着关键性的作用。这两位人物一是黄宾虹,一是王铎。
林散之的书法历程粗略大致可分为四个阶段,30岁之前的对传统书法文本的形质体察期;30岁后拜黄宾虹为师至上世纪60年代中期阶段,这一阶段是林散之深悟中国水墨精神的体察期和外师造化的实践期;60年代中期至上世纪70年代初是沉浸于王觉斯为代表的明清之际草书大家的转轨变型期;上世纪70年代初至80年代末的晚年,是他书法艺术的成熟期。
黄宾虹对林散之的影响,贯彻了林散之的一生,由于林散之对黄宾虹的顶礼膜拜,林散之30岁至上世纪60年代中期,他的书画基本是黄宾虹的衣钵和艺术语境。黄宾虹是中国山水画的集大成者。林散之在黄宾虹身上深刻领悟了笔墨在中国传统书画上所表现的生机,他成功地将黄宾虹的“五笔七墨”之法移植到他的大草作品中,因而使“林草”的线条有别于前人,且具有丰富而神秘的色彩。林散之悟性过人,在众多明清之际的大家中,林散之在书法转轨思变阶段,独具慧眼最钟情的书法大家却是王铎。这里再提一下王铎,明清之际,是草书大家辈出的时代,然明清之际诸家多于长笺巨幅振笔疾书,但求痛快淋漓,缺少蕴藉之致,草书易犯率滑尖刻、拖沓之病。林回避了这些不足,林散之在王铎那里逗留的时间应该是很长的。林散之“以王觉斯为友”的说法,应是肺腑之言。原因大概是王铎是追慕晋人风骨的。王铎虽是二臣,但在改朝换代的历史更替中,他的生命意识宕荡,他与黄庭坚相比,书法文本层面丰富,灵性充沛,他个人书写的情性较之历代大家都更具奇险。反常易变的特性且有所不羁,使他的线条似乎总带有某种不确定的力量。王铎的书法常有越出习俗的意外转换,也反映了他内心对既定秩序的怀疑和不认同。王铎尝试用大团的涨墨调节书写空间和节奏。他力图将大块的墨团浸润,与枯笔的互动相映,这种满纸烟云,别开生面的形式效应无疑使林散之产生了共鸣。“林草”在这些方面吸取了王铎的丰富营养,直至与王铎神会而归。
基于这种说法,林散之由于对黄宾虹和王铎艺术精神的把握,使他的草书更具诗情画意般的光彩和天真烂漫的意味。林散之挚友邵子退的诗说得很形象:“先生作书如作画,春蛇入草秋藤坠,先生作画如作书,铁画银针笔不枯。”赵朴初居士诗云:“散翁当代称三绝,书法尤矜屋漏痕,老笔淋漓臻至善,每从实处见虚灵”,“风雨潇潇惊笔落,精神跃跃看花开”。这些都是对林先生诗情画意,天真烂漫的书法的形象描绘。
把林散之放在书法历史长河中阐释,不难看出,林散之在秉承“魏晋之魂”的精神层面上,在继承传统上,在书法意境和书写表现技巧上,都成功地拓展出了一个广阔的空间,林散之在前人面前有了新的创造和发挥,因而林散之的名字应该是彪炳千秋的里程碑式的人物!
三、作为传统文人,林散之平实人生使他成就了“道德”和“文章”两个方面。
传统文人在追求“文章”事业的同时也是十分讲究自身的“道德”修持的。作为一种道德的修持,林散之在做人方面崇尚的是与书法本真精神相一致的大“道”大“德”。他说“搞艺术是为了做学人,学做人。”“做学人,其目的在于运用和利人”。“做学人还是为了做真人。”从林散之这些笔谈中,我们不难看出,林散之求艺和做人都是求的一个“真”。由于林散之秉持的是大“道”大“德”,因而他面对争名于朝,争利于市的市井现象始终能以淡泊自甘的生活态度置之。他“笑把浮名让世人”,平生习惯地过着“写罢倚南窗,无言空默默”式的平民生活。他与世不争的大德人品,表现的是道家“无为和守静”,而他所追求的是能与古人争一席之地的“实”,这是他处世的“真”的一面。晚年的林散之,身名海内外,他曾是江苏省书协名誉主席,南京书画院院长,全国政协委员,但在林身上看不到一点“僚气”和“霸气”。他无偿创作的作品数以万计流落民间,为了“利人”他甚至能乐意为乡民子女进厂求工作作书,民间藏有大量林先生的作品,人们昵称林散之是“林半吨”,但他也从不介意,乐在其中。林先生对委身攀附于权力的势利小人鄙之为不齿,他的谦逊、重情、仗义在民间有口皆碑。在日伪时期,他以自己在地方上的名誉,枪下救人;在国难当头的时日,他痛心疾首,以文人特有的表达方式,写下了多首忧国忧民的感伤之诗。在面临洪水泛滥之时,他身为圩董,公而忘私,舍生忘死,带领乡民开展自救。他平生沉默寡言不打妄语。这些都是他平生持守的“大道”“大德”的自然流露,没有一点为了某种政治需要和个人利益而故弄玄虚,招摇撞市。他的品行和他的书法一样“货真价实”。林散之是个非学院派成长起来的书法大师,当有关部门请他申报技术职务时,问其何等学历有何成就时,他诚实地写下了“余一生写字画画,其实一概不是!”的大实话。他身为江苏省书协名誉主席,招他去开会,他竟然认为怎么会有书协?竟然不知自己是书协的名誉主席。林散之这方面的“呆”,恰是他童真、率真的天性流露。
南京的杜方平挽林散之的对联“名利置度外,草圣仍平民”是对林先生人生的很好概括。林散之用他的言行和他亘古耀今的绝艺向世人昭示:他不愧为真正意义上的“德艺双馨”的艺术家,不愧于中国当代书法上的一块丰碑!